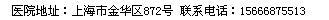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痔疮 > 痔疮危害 > 原创安自求逆境磨砺
原创安自求逆境磨砺
母亲不幸离世,对我是一次惨重的打击,是无法抹去的创伤。然而祸不单行。俗话说:一歪三乱蹿,一蹿就蹿好远。母亲病重期间,我被安排到县知识青年训练班学习,准备派到麻城、蔪春参加社教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是作为接班人培养和锻炼的,全县共有一百二十四人参加培训,其中还有十四个大学生。我因母亲病危,中途退出,回家后在母亲床前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她老人家去世。这次不仅使我失去了慈爱的母亲,也使我在人生中失去了一次经受锻炼和被培养的机会。当时在训练班学习的有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万占鳌、徐东旭、陈守仕、黄开恒、黄朝玉等人。后来他们都担任过乡镇书记、乡镇长等基层干部。也是我没有当干部的命,话说回来,就我的个性就算当干部也当不了好长时间,就会被淘汰。所以我也无怨。母亲去世后,我在家住了将近一个月,公社领导安排我到学校代课。一九六六年七月份又将我调回公社当农技员,并代理团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一起,在公社所在地背后的生产队驻队。当时,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相继成立,我们开始时还被造反派打成了保皇派。那时干部是走资派,不造反的人就是保干部的保皇派。在别人的劝告下,随大势所趋,也是怀着一腔拥护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感情,凭着青年人一股激情,投入了运动,还当上了负责人(公社革委会主任、“造反兵团”头头之一)。但到了运动后期,被“莫须有”的定为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开除工作回家劳动改造,连我的爱人也受株连,同时遗返回家。在全公社批斗大会上有人呼出了“打倒坏分子安自求!”的口号,更有甚者,有人居然写字条传到台上,写着“打倒安自求的臭老婆丁小红!”我当场抵制,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牵连无辜的爱人。幸亏小红当时不在场,不然定会气得吐血。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欲置我于死地,说我顽抗到底,不老实认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在学习班时被规定“三不准”:一不准写信,二不准打电话,三不准和亲人见面。工作队如临大敌,荷枪实弹,把我们押进押出,严厉看管,不许随便说话和走动,连上厕所都有人监视。白天劳动,打战备洞,到草盘区星光大队的大山上和桃花冲山上砍柴、挑柴;夜晚学文件、写检讨、开批斗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那时在学习班的学友(实际上是难友)有安庆祥、田海等人。好在我们是鼓里的麻雀——吓大了胆,也习以为常。小红和我结婚只有半个月,想借送菜的机会去看看我,通过了岗哨检查,刚进去,正赶上吃晚饭,我把一碗饭分做两半碗叫她在旁边低头吃。凑巧被学习班负责人段友成发觉,大声呵斥。叫她“滚蛋”,还要追究门卫和我的责任。小红一口饭未吃,含泪走了,幸亏被老乡刘和权(他当时在学习班当指导员)路过看见,叫小红到他家去。小红哭了一夜,也一口东西未吃,第二天一步一蹿回家,大病一场,又没人料理,天天以泪洗面。当天夜晚我也一夜未眠,上半夜开批判会批斗我,还要我写检讨;下半夜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响应领袖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化大革命”,却落得如此下场,连我的亲人都无辜受到牵连,老父亲党籍被开除,小队长被撤职,小红被迫离开学校,回家生产。真是感到比窦娥还冤!俗话说:“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一九六九年,我县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洪灾,田地、房屋垮塌无数,陶家河也是一样,为了恢复洪灾创伤,我们一天到晚搬石头、挑土填被洪水冲毁的田地,又没有东西吃。又累又饿,好几次几乎昏倒。政治上的打击,精神上的创伤,繁重的体力劳动,饥饿的折磨,不知世事的人的冷眼,同情者的好言宽慰,无不刺痛我的心,人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求生的本能支撑着我,含冤受屈又不甘心倒下的我强忍悲愤,自信自己不是坏人,即使有错也不全在我,总有一天能见天日,还我清白。那时候,生活苦不堪言。很少吃米,主要吃国家救灾供应的红芋渣饼,合着茅香,铁菱角粉煮糊糊喝。甚至有人吃观音土和节节绊、青蒿一类的草。我垸有十二户,有十户出去讨过米,只有一位干部和我家没去讨。有一天,实在揭不开锅,妹妹提个篮子想去讨米,被我看见,我坚决不要她去。妹妹含泪到田里扯了半篮节节绊草,切碎煮熟把点盐,没有油,一人一碗,边吃边流泪。一家人饿得有气无力,都饿变了相。我原先在公社时又白又胖,体重一百二十多斤,回家后不到两个月,人又黑又瘦,体重不足一百斤。为了忙点钱,我和小红到夏河驮树到红花,路过占河街。街上的人都不认得我。公社隔壁肖大娘向我看了又看,问我:“你这个哥是原来在公社的小安的哥还是他兄弟呀?”我苦笑着说:“大娘,我是他哥哥的弟弟,弟弟的哥哇!”大娘抹了一下眼泪说:“多好的一个小伙子怎么成了这样啊!”她再三叫我们到她家坐一坐,拿出两个红芋拌细糠做的粑给我们,我夫妇二人如获宝贝,千谢万谢。几十年过去了,慈祥的大娘早已不在人世,但她那善良的举动我终生不忘。小红还翻山越岭从陶河挑黄金叶到红花,每天忙到八毛至一元钱。饥不择食,有一次我饿得无法,吃茅香、野菜,吃多了几天大便不通,腹胀如鼓。造成痔疮,肛门裂并发,便血不止,险些丧命。后来喝了两碗蜂蜜水(岳母和舅娘给的),跪在厕所里双手撑地,膝盖着地,挣得大汗淋漓,泪水直流,过了约半个钟点才挣出一坨大便,打在粪坑里像一块石头掉到水里。原来是吃下的茅香在肠道里结成了坨,堵塞了肠道和肛门。解出的像石头一样的血坨子,撬开一看,一层一层的茅香裹成了团。从那以后,经常便血。万般无奈,在大儿建军出生的第三天,我瞒着家人,含悲忍泪,偷偷地和同垸的叔父安祥咏,表叔汪从宽一阵到离家一百二十多里的马家河大山上砍树、驮树。可怜我一介书生,体弱多病,又不在行,白天在山上砍树、锯树,累得筋疲力尽,收工时还要驮一根木材到木材场,一般都是一百五十斤以上,夜晚别人打扑克,说笑话,我拿个小板凳坐在稻场边,对着家乡方向遥望着。想念刚生孩子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还有年迈的父亲,年少的弟妹不知他(她)们怎么样了。坐到夜深,露水打湿了衣裳也浑然不觉,直到半夜后才上床睡一会儿,天刚亮就起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工友们一道一步步艰难地走向深山老林……。时间一长,身上破衣烂衫、伤痕累累,眼窝深陷蓬头黑面,人都变得麻木了,也不爱说话,更没笑过一回,真是度日如年,欲哭无泪。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悲凉啊!有一次在锯大树时,“过山龙”(锯名)卡住了,大树突然倒下,我退让不及,眼看就要被倒下的大树砸成肉饼,也可能是苦人真有天照,也可能是我命不该绝,我忽地弹起摔出一丈多远,睁眼一看,原来是旁边的一棵小树把我弹到一边,使我逃过这一劫。死罪侥幸逃脱,活罪却难逃。过了一段时间,山上木材要人工往下运,从山上树林到山下木材场,最近的也有五里路,最远的有八里路,山路崎岖,空手都难走,何况还要扛上沉重的木材。有一次我扛了一根两米多长的树,重约二百多斤,我在别人的帮助下才扛上肩,谁知越驮越重,开始还能扛上两三丈远打一杵,后来丈把远就要打杵,换个肩,喘口气,咬紧牙关一步一挨,天快黑了,别人都下山了,深山老林里野兽多,一会儿听到豺狗叫,一会儿听到野猪或不知名的野兽在山林中弄得噼噼啪啪响,真是叫人毛骨悚然,心想把树丢掉,空手下山,但一想到在家做月子的妻子连饭都没有吃的,还有出生不久嗷嗷待哺的儿子和整天愁容满面、唉声叹气的老父亲和弟妹,都指望我挣点钱回去救他们时,我只好横下一条心,拼命也要把树驮到场,天黑了,我才一步三点头地到达木材场,我放下树,就随树倒地起不来了,腰痛得直不起来,嘣嘣响,待我回到树棚,便倒在床上起不来了,连晚饭也没吃一口,只喝了一口水,这样在床上连躺三天,找不着医生,也买不到药,还是好心的房东赵敬文老板到山上扯草药给我敷,又到三十多里外的街上给我买了些伤痛膏贴,我才勉强能下地走路。不得已只好回家,准备伤好了再去。谁知,疾病上身,神经衰弱、胃溃疡、肠炎、痔疮、肛门裂、风湿性关节炎、腰痛等多种疾病接踵而来,大病一场,卧床一个多月,在床上翻不了身,坐着也起不来,走路要人搀,吃饭都要人喂。有一天,我趁家里无别人,从床上慢慢滚到地上,爬到后门口,拄着一根棍子,一步步挨到后山,想找块准备葬自己的地方,晚上我强忍悲痛,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并叫她带孩子改嫁,只是孩子不要改姓,妻子听了大吃一惊,坚决不同意。她倾心安慰我,精心照料我,四处奔走,求医问药,甚至求神拜佛,为我治病,使我好不容易闯过了这道鬼门关。可是肛门旁又长了漏管,俗名叫“老鼠拖粪门”,简直痛死人。一发作时,人痛得在床上翻跟头。后来还是肖建勋老师带我到草盘萧家大屋,找到专治跌打损伤和怪疱奇疮的民间医生肖锡淦,买了他祖传秘方制成的十张膏药,才将漏管拔出来,让我逃出苦海。在家劳动了半年,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干部都调离了原单位,公社领导也换了人,原来的对头人走了,新来的书记黄伟如了解我的情况后,安排我回学校继续教书,陶河大队干部也三番五次到我家做工作,当时,我执意不肯回学校,还驮着肩担上山去砍柴,不理他们,因我的怨气在胸,对干部反感,后来以汪成钧为首的几位老同事上门邀请,我才勉强上班,但随时准备回家生产。这次我被遣回家虽只半年时间,在我的人生史上是最艰难,最危险的岁月。我饱含悲愤,受尽屈辱,吃尽了苦,受够了疾病的折磨,居然活了下来。我暗暗发誓,再不踏入官场半步,不向邪恶低头,一心一意教书,从此与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苦在其中,乐在其中,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无怨无悔。少年时读书半途而废,青年时母亲早逝,风华正茂时因一场政治运动而得罪了官老爷被打成了“坏份子”、“反革命”,生活艰难,劳累过度,身心受损,中年以后受尽了疾病的折磨,开了三次刀,第一次是胃溃疡险些穿孔而将胃切除五分之三;第二次是割痔疮,解不出大小便,妻子用钥匙往外掏粪便,用胶管导尿;第三次是脊椎骨折,手术时用两块钢板固定,半个月不能动弹,至今钢板还在体内,不能弯腰曲背,不能用力,成了半残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我是一粒铜豌豆,压不碎,打不烂。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些别有用心的坏蛋妄图以各种不实之词整垮我,要我喊“打倒安自求”,我就喊“毛主席万岁!”要我认罪,我就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只认错,不认“罪”,被批斗后,我唱毛主席语录歌,连吃三大碗饭。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借题发挥,说我支持右派分子李敬群和国民党伪团长安绳祖翻案。支持李敬群确有其事,“文革”刚开始时,草盘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当时的区委干部,草盘区文革领导小组派人找到原来受区委打击迫害的李敬群去批斗区委一班人。原来李敬群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当时区干部到学校打球时打伤了一名学生,作为老师的他,以为自己是在朝鲜战场立过功而复员的军人,不怕那些恃强凌弱的人,便挺枪出马为学生说话,却遭到那些干部的辱骂,还扬言要开除他,愤慨之余,李就在街上写出了“小小教师低人一等,区乡干部仗势欺人”的大横幅标语。李敬群的右派就是以此为罪名而定的。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反对干部就是反对党,而被开除回家劳动改造。他的问题一拖就是十年而未得到解决,草盘开批斗旧区委大会,李也认为机会难得,可为自己讨回公道。我在别人再三劝说下,就为李敬群写了一张字条:“区文革负责同志:今有我社李敬群来你处,请接洽”,此纸条被人留作我支持“坏人”的证据。后来,李敬群跑到北京找到他在朝鲜战场上团首长,获得首长批示。李敬群以此作为材料用大字报的形式到处张贴,强烈要求为自己平反,可是运动后期却又遭打击,被批斗、关押。他见平反无望,穿好衣服,躺在棺材里不吃不喝,含恨而死,以此抗争。安绳祖,据说是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抗战爆发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团长,后因团长阵亡后,由他代理团长,带部队守卫四行仓库,后遭日寇飞机轰炸,医院治疗,解放后一直把他当作反动军官对待,坐过牢,因病保外就医遣返回乡。我原本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面。然而在批斗我时,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支持伪团长安绳祖翻案,因为是同姓,辈份年龄安绳祖比我大,说我是他的孝子贤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如果按此推理,大汉奸汪精卫是卖国贼,是不是汪姓后人也都是卖国贼?蒋介石是反革命头子,那么蒋姓的人都是反革命吗?还有人大放厥词,说我“出身不好,小时不是个好东西,现在不是个好东西,将来还不是个好东西。”我回答他:“我是个人,不是东西,是不是好东西要看结果。”有谁知,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自古至今无一人例外。由于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环境不同,经历有别,人生也不同。有的人一生潇潇洒洒,尽情享乐;有的人,劳碌奔波,只求温饱;有的人富足过剩,为金钱所累还不知足;有的人因天灾人祸不得安生。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家家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有三怕:一怕穷,二怕病,三怕老。穷,别人看不起,自己日子也难过。老了难,自己苦,别人嫌,“病来如山倒”,“好汉就怕病来磨”。几十年的艰苦经历,使我患有神经衰弱、眼角膜炎、牙龈炎,心律不齐,胃溃疡、肠炎、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胃切除手术后遗症,使我不得安宁,每年冬季胃肠炎复发,夜不能寝,吃也差很多,右眼视力只有0.4,肩周炎导致右手麻木,心血管肌桥导致心血不足,腰椎骨折,固骨的两块钢板至今还未取出,睡觉和弯腰都困难,左肩骨折虽已治好,天阴下雨仍隐隐作痛。几十年来,不知吃过多少药,花了几多钱,熬过多少不眠之夜,闯过了一道道死亡线。经过近几年的治疗,虽大有好转,但顽疾难除,但我仍坚持锻炼,积极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的一生坎坎坷坷,除生活的折磨,病痛的煎熬,还曾五次遇险:一九六七年在西硔水库参加游泳比赛,因出意外,险被淹死;一九七〇年在英太寨黑石塔上扯秧草,失足坠岩差点跌死;同年八月在霍山马家河山上砍树险被大树打死;一九九五年因心肌缺血,过度虚弱,晕倒一个多小时;一九九七年因心律过缓,造成骤停,几乎猝死。每每谈及此事,众人感叹唏嘘不己,族叔庆祥曾口占小诗一首,记录如下:“举头三尺有神明,天公赐寿佑苍生,五死一生传佳话,恩传后世不了情。”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挨批斗,还是被遣送回家生产,过度的劳累,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我都挺过来了,天生倔强性格,不信邪,不怕“鬼”,在邪恶面前不低头,在逆境中不灰心,自认为做到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襟怀坦荡,磊落光明。既不是懒汉懦夫,更不是奸诈小人。作者简介;安自求,湖北英山人。在陶河中心学校从事基层教育工作。36年如一日,十年教导主任,二十年校长,三年校党支书记!为家乡教育呕心沥血。而今皆桃李天下!本文选载老师作品〈心迹留声〉!特别申明:本文版权属于原创作者,严禁转载!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治疗白癜风最专业的医院北京治疗白癜风一共要多少钱